理论成果 
碰撞,来自法律本身
本文刊登于《法律与生活》1997年第2期第40页
碰撞,来自法律本身
杭 正 亚
改革开放的中国打开了市场经济的闸门,犹如赛场的激烈市场竞争席卷赤县神州。这里既有“合理碰撞”,也有“故意犯规”这就需要法律作出裁判;然而,假如法律本身产生了碰撞,又该如何是好?
谁能想到,一个本来并不复杂的纠纷,由于某些莫明其妙的行为,使得七、八家单位卷入了一场诉讼,引发了两家法院的冲突,最高人民法院两次正式书面批复,笔者作为一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为之奔走呼号,历经四年,感慨万千……
案由:租船纠纷耶,购销纠纷耶?
1992年7月16日,深圳新直工贸公司(下简称深圳公司)驻天津塘沽中转处(下简称深圳中转处)与江苏省启东市对外贸易公司(下简称启东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由深圳中转处向启东公司出售煤炭10万吨,每月供2万吨,南通港交货。要把煤炭运到南通,就要海轮。于是,深圳中转处在7月30日与武警学院晋中煤焦运销处(下简称运销处)驻塘中转站(下简称运销处中转站)签订联营协议,约定由深圳中转处负责煤源,运销处中转站负责提供船只运到南通姚港码头。
1992年8月7日,运销处又与江苏省兴化宏达集团(下简称兴化集团)签订一份合同,约定运销处于同年8月供给兴化集团2万吨煤炭,南通姚港码头交货,供方的义务由运销处中转站负责实施。合同签订后,兴化集团先后向运销处中转站支付货款计185万元。
8月28日,运销处中转站与烟台开发区金东船务公司(下简称船务公司)签订租船协议,约定由船务公司调“智海”轮为运销处中转站运煤,该协议还约定了仲裁条款。协议签订后,运销处中转站从兴化集团预付的货款中,先后支付运费计87万元给船务公司。8月30日,运销处中转站又与深圳中转处签订“转让租船智海协议”,约定将“智海”轮的租用权转让给深圳中转处,由深圳中转处到天津港货运公司(下简称货运公司)办理手续,收货人由深圳中转处确定。
9月9日,深圳中转处又与启东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由运销处中转站担保,约定启东公司从深圳中转处购煤炭2万吨。协议签订后,启东公司几次支付货款共295万元,深圳中转处用此款购得2万余吨煤炭。
这样,一条“智海”轮,一个航次,一批2万吨煤炭,却允诺了两个需方,两个需方都分别从自己合同的供方手里得到货轮的有关资料的复印件,等待着“智海”轮抵达天津新港装煤运到南通。
好象一个姑娘,许诺了两个婆家,岂能永远隐瞒!
9月15日,“智海”轮靠岸,兴化集团经办人发现运单上的收货人是启东公司、海门燃料公司,当即找运销处交涉。运销处的“高参”们,为了避免运销处走上被告席,便在9月17日抢先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以船务公司违约装载深圳中转处的煤炭为由,要求被告船务公司和第三人深圳中转处、货运公司赔偿损失。
明明是自己转让了租船合同,却说成是别人违约装载;明明是侵权人,却把自己打扮成受害人!
当日,天津海院以租船合同纠纷为案由立案,后又通知兴化集团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经合议庭主持调解,各方达成协议。9月21日,天津海院以(1992)津海法商调字第66号民事调解书确定:“智海”轮本航次装载的20578.6吨煤,收货人由启东公司、海门燃料公司变更为华能南通电厂(兴化集团指定的收货人)。货运公司当天履行了调解书所确定的义务,致电南通姚港变更收货人。同日,兴化集团将存有180万元的存折交给深圳中转处。次日,因深圳中转处到银行取不到款,由天津海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将款划到深圳中转处帐户。
9月29日,正当“智海”轮准备履行天津海院的调解书,向华能南通电厂卸煤之时,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启东公司的申请,裁定扣押了载于“智海”轮的全部煤炭,随即又处理了煤炭并保全货款。后来,启东公司向南通中院起诉深圳公司,南通中院以购销合同纠纷为案由立案。
真可谓,你打鼓,我吹号,各奏各的调。两个法院以不同的案由立案,诉讼标的物又是“智海”的同一航次煤炭。究竟以哪个法院的审理为准?兴化集团经办人手捧那张无法执行的调解书到处上访,受到最高法院和各地方法院的热情接待。但是,他们意见各异,众说纷纭:
有的认为,本案是租船合同纠纷,天津海院的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应当得到履行和执行。如果认为该调解书确有错误,也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而不能由其他法院运用财产保全的措施阻止它的履行。
有的认为,本案实际上是购销合同纠纷,不是海事、海商案件,天津海院无权受理,而且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南通中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是正确的,受理案件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兴化集团如要保护自身利益,只有在天津海院撤销民事调解书后,另行起诉。
有的认为,本案既有租船合同纠纷,又有购销合同纠纷,两个法院的审理都合法。兴化集团与被扣押的煤炭紧密相关,应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到南通中院参加诉讼。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弄得兴化集团无所适从。本来认为没有违约,打官司不找律师也不会吃亏的兴化集团,不仅未能得到煤炭,相反又被诉讼的旋涡卷走了巨额货款。这时他们委托兴化市第一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代理,笔者从此参与了这场马拉松式的诉讼。
代理案件先看案由,这里的案由问题又关系到诉讼能否成立。如是租船合同纠纷,南通中院就不能受理;如是购销合同纠纷,天津海院就不能受理。经过分析,我们可以从法律关系上看出,当事人之间有着:一是启东公司与深圳公司之间和兴化集团与运销处之间的两个购销合同关系;二是运销处与船务公司之间的租船合同关系;三是深圳公司与运销处之间的联营合同关系。既然有租船合同关系、购销合同关系,当事人又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不论其诉讼请求是否正当,法院分别以租船合同纠纷、购销合同纠纷为案由立案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主要矛盾体现在购销合同纠纷上,租船合同纠纷不过是有关当事人虚晃一枪而已。
争执:管辖异议耶,审判冲突耶?
1992年12月初,我们经过北上南下,走访有关法院,获悉到:天津海院已向天津高院报告,请求最高法院指定,由该院并案审理。南通中院也向江苏高院报告并转最高法院,认为运销处诉船务公司租船合同纠纷一案,因该合同有仲裁条款,天津海院对该案无管辖权;而启东公司诉深圳公司购销合同纠纷一案,交货地点在南通,南通中院有管辖权。
两家法院都在等待着最高法院的定夺,案件第一次搁浅!我们的工作该从何处着手呢?
兴化集团与运销处之间的购销合同关系,天津海院审理租船合同纠纷时作了合并处理,但是未能得到履行。这一问题较复杂,必须向两个法院的共同上级法院,即最高法院申诉。而天津海院从兴化集团帐户上执行180万元给深圳中转处,民事调解书上并无此内容,向天津海院申请执行回转法律关系并不复杂。
我们在天津突然获悉,兴化集团的180万元货款已被深圳中转处转移到唐山,而该处已于1992年 9月30日被天津市塘沽区政府经协办撤销,便向天津海院申请执行回转。该院非常重视,于12月29日在唐山强行将180万元划到天津海院帐户。后来,该院连同向运销处追回的货款53270元,共计人民币1853270元汇给兴化集团。
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下面就是向最高法院申诉了。
1993年3月初,最高法院有关审判庭的审判员接待了我们。他们看法不一,有的认为两个法院争执的性质是管辖争议,天津海院无管辖权,应移送南通中院审理;有的认为不是管辖争议,而是法院之间的矛盾,应协调解决。
所谓管辖争议,是指两个以上人民法院对某个案件,都认为自己有管辖权,或者都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天津海院、南通中院审理的案件,案由完全不同,当事人也完全不同,根本不是管辖权争议。这是一种法律上尚无明文规定的、法学界尚未展开研究的、审理程序上的争执,笔者暂且把它叫做审判冲突,即同一法律关系或同一诉讼标的物,由于两个以上的法院审理,产生了两个以上不同结果的法律文书,各个法院竞相要求履行或者执行,使之发生矛盾和冲突。目前只能由最高法院协调解决,而不能移送管辖或者指定管辖。1993年3月底,我们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书面请求,申明我们的观点,请最高法院从速决定。
1993年6月16日,最高法院发出法经(1993)114号函,认为:天津海院在审理运销处诉船务公司租船合同纠纷一案中,将与之性质完全不同的煤炭购销合同纠纷合并审理,且在利害关系人启东公司没有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将载于“智海”轮上的煤确权,显属不当。应撤销(1992)津海法商调字第66号调解书有有关部分。南通中院审理的启东公司诉深圳公司、运销处购销合同纠纷所争议的载于“智海”轮上的煤炭,实质上涉及启东公司与深圳公司和兴化集团与运销处两个购销合同。因此,南通中院应通知兴化集团参加诉讼,将两个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合并审理。
审理:合并审理耶,分案审理耶?
南通,1993年7月上旬,气候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但走进南通中院经济审判庭的我们,却感到一阵阵舒适。舒适,不仅是因为空调带来的凉爽,更由于最高法院114号函的下发,使得我们告状有门了。
看来我们高兴得过早了,我们被告知,最高法院要求合并审理的意见无法执行,天津海院不撤销民事调解书,不将材料转来,南通中院无法审理,疑惑和失望凝聚在空间,似乎温度也升高了。
我们又赶到天津海院,该院答复,最高法院只是要我们撤销调解书的有关部分,而不是撤销整个调解书,更没有要我们将材料转到南通中院去。
两家法院仍在抗衡,案件第二次搁浅!
又是几个月的北京、天津、南京、南通之间的穿梭上访,最高法院又出面协调,南通中院终于同意受理。但是,对于兴化集团的诉讼地位问题,最高法院与南通中院的意见不一致。兴化集团要求以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申请、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起诉,均被南通中院所拒绝。显然,南通中院是要分案审理。最后,兴化集团只能以原告的名义、以购销合同纠纷的案由,起诉被告运销处、深圳公司。
1994年5月中旬,我们来到被告运销处的登记住所地,早已无运销处的踪影。与这样的被告打官司,打赢了又如何执行?
我们当时似乎感到,一个注册资金85万元的企业岂能无影无踪,它的注册资金很可能是虚假的。经调查,发现山西某审计事务所只凭武警学院同意拨给运销处汽车和经费的函,就为其开业验资,档案中没有车辆的过户手续和拨给经费的银行凭据。
这样,兴化集团便向南通中院申请追加武警学院为被告。
1994年12月22日,南通中院开庭。庭审,在合议庭的精心组织下,逼近核心。武警学院、运销处方承认车辆和经费没有拨付,但又说拨付了其他价值相同的物资,并且拒绝回答和举证是什么物资。同时,他们对南通中院不合并审理的做法,提出了非议。
1995年4月25日,南通中院作出(1994)通经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运销处返还兴化集团货款并赔偿损失,深圳公司、武警学院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送达后,运销处提起上诉。另外,他们又向最高法院反映,南通中院未按最高法院批复合并审理。随后,最高法院经济审判庭发出(1995)第267号函,要求江苏高院中止审理。
案件第三次搁浅!
1995年11月,我们又到最高法院,向有关领导和承办审判员反映了本案诉讼的艰难,呈递了书面请求。1996年1月8日,最高法院发出正式书面批复:
关于对江苏省宏达集团诉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晋中煤焦运销处购销合同纠纷案及相关案的处理意见
法经(1996)15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我院以法经(1993)114号函对天津海事法院审理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晋中煤焦运销处(下称武警学院运销处)诉烟台开发区金东船务公司、第三人深圳新直工贸公司驻天津塘沽中转处、天津港货运公司、江苏省兴化宏达集团(下称兴化集团)租船合同纠纷案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启东市对外贸易公司(下称启东公司)诉深圳新直工贸公司、武警学院运销处购销合同纠纷案提出处理意见后,武警学院运销处致函我院,反映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不按最高人民法院函复意见办,请本院予以解决。本院审查了有关材料,经复议认为:
一、启东公司诉深圳新直工贸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与兴化集团诉武警学院运销处购销合同纠纷案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上述案件分开审理是正确的,本院法经(1993)114号函提出将上两购销合同纠纷案合并审理的意见不准确,应予更正。
二、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启东公司诉深圳新直工贸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已发生法律效力,应依法进入执行程序。
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兴化集团诉武警学院运销处购销合同纠纷案中,深圳新直工贸公司与武警学院运销处之间系协作型联营关系,将深圳新直工贸公司列为上述案件的被告不当,请你院在二审中予以纠正,并公正审理本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章)
一九九六年一月八日
1996年3月7日,江苏高院经济庭开庭审理本案。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南通中院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上诉人认为,由于最高法院改变了并案审理的决定,南通中院对本案就没有管辖权。我方认为,合同的约定履行地在南通,依据民诉法第24条,南通中院有管辖权。2、运销处是否已经履行合同。上诉人认为,经天津海院审理,运销处已经履行合同,交付了“智海”轮上的煤炭;我方认为,最终装上“智海”轮的煤炭是深圳公司所购,只有运销处在南通将煤交给兴化集团,才能视为履行合同。3、运销处是否具备法人资格。上诉人认为,运销处具备法人资格,不应追加武警学院为被告;我方认为,运销处不具备法人资格,且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本案证据足以说明开业时的验资是虚假的,只能由其开办单位武警学院承担民事责任。
1996年9月18日,兴化集团收到了江苏高院(1996)苏经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武警学院退还兴化集团货款 1796730元,承担违约金173000元,支付利息损失581500.83元,共计人民币2551230.83元。
终审判决,终于在人们等待了四年之久后,姗姗来迟!
思考:冲突的原因与解决的办法
一场诉讼结束了,但是它却引起人们的深刻思考:
纠纷本来并不复杂,为什么还要最高法院多次协调、两次批复?为什么要进行长达四年的、马拉松式的诉讼。复杂的是法院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使得合法权益不能及时有效地保护,违法行为不能及时有效地制裁。这种现象既不利于维护我国法制的尊严和统一,又要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有效的控制。
1、从法的遵守上来看,当事人损人利己、规避法律,是引起冲突的事实原因。运销处违约引起了纠纷,为了转嫁危机,便制造了一个租船合同纠纷的案由,抢先在当地法院起诉,把守约者推上被告席或者充当第三人。兴化集团知道他们诉讼的目的是为了变更收货人,也乐于参加天津诉讼。启东公司明知天津海院审理却不愿参加,而是到当地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并以购销合同纠纷的案由起诉。在纠纷及诉讼中,当事人往往从经济上考虑得多,从法律上考虑得少;从自身利益考虑得多,从他方利益考虑得少;从可能性考虑多,从可行性考虑得少;从眼前利益考虑得多,从长远利益考虑得少。更有甚者,有奶就是娘,只要对己有利,什么规避法律的事都敢干。对于这种挑词架讼、钻法律空子的当事人,决不能让其占便宜。解决办法就是人民法院明察秋毫,除驳回起诉或者驳回诉讼请求外,还要予以民事制裁。同时,还要注重保护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2、从法的适用上来看,法院之间各自为政、缺乏沟通,是引起冲突的司法原因。同一船煤炭,两家法院作出不同的处理,造成一物两“判”,值得深思!尽管最高法院多次协调,但由于认识不统一,对于案件是否要移送管辖、是否合并审理、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等等问题,各持己见,僵局当时并没有打破。曾经有人戏曰:最高法院都难以解决问题,难道还要把案件交到国际法院!法院之间发生了冲突,如不能迅速解决,定会损害执法机关的形象。这种冲突是审判机关内部的问题,积极地、主动地予以解决这是审判机关的责任,而不应等当事人上访、申诉了,才去消极、被动地解决问题。赛场上运动员发生碰撞,裁判一鸣笛,问题就解决。诉讼中的“裁判”发生碰撞,不仅使当事人无所适从,而且比当事人的纠纷更难解决。当事人有纠纷可以起诉打官司,法院之间有纠纷如何解决?笔者认为,法律问题必须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这就要从法的制定上找原因。
3、从法的制定上来看,法律规范不尽严密、完善,是引起冲突的立法原因。目前的民事诉讼法律规范,还不是那么严密而完善。比如对于案由审查的规定、合并审理的条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等等问题,规定尚不具体,法院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执行。当前立法与司法解释的现状是: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诉讼的某些情况发生变化,而立法滞后;另一方面,司法解释与相关法律不尽统一。使得司法机关可以各取所需,任意解释,形成冲突。而对于冲突的处理,尚无明文规定,目前只能通过自行协商或共同的上级法院协调解决。这种办法缺乏应有的权威性、规范性、时限性,效果不佳。难怪下级法院可以对上级法院甚至最高法院的协调意见拒绝执行,造成诉讼活动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就说明立法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及时地、正确地把诉讼活动中存在的客观规律反映在法律之中。
(作者单位:江苏扬州兴华律师事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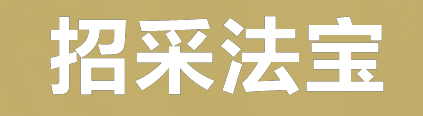

 2021-12-10
2021-12-10  浏览次数:次
浏览次数:次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